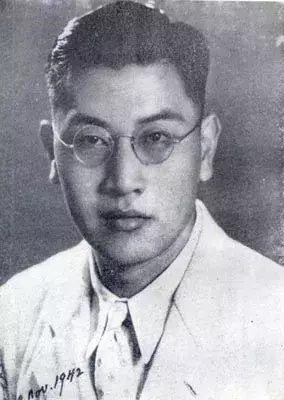星来星去,宇宙运行,春秋代序,人死人生,太阳无量数,太空无限大,我们只是倏忽渺小的夏虫井蛙。
——戴望舒

你也许不知道戴望舒是谁,但是你一定知道那首唯美哀伤的《雨巷》。
“撑着油纸伞,独自彷徨在悠长,悠长又寂寥的雨巷 。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 。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 ,丁香一样的芬芳 ,丁香一样的忧愁 ,在雨中哀怨,哀怨又彷徨 。”
诗人戴望舒一生的爱恨情仇仿佛都是从那一段雨巷开始的。

1927年,那是一个下雨天,年轻的诗人戴望舒撑着油纸伞,独自穿过一个狭长的巷子。
脚下是湿漉漉干净的地面,黑的砖,红的瓦,风景是好风景,但它们和密雨一起徒增了他的愁绪。
他满怀心事地走着,来找好朋友施蛰存。
此时的他,正值大革命失败,烦闷不堪之际,来好友处小住,权当是散心解闷。
施蛰存是《现代》杂志的主编,也是戴望舒的知音,他欣赏他的才华。
起初,并没有人看好戴望舒写的诗,正是施蛰存在《现代》杂志上主推他的诗,并给予高度评价,他才一步一步被大众所熟知。
戴望舒在雨巷中走着,这条漫长的雨巷,像极了自己的忧愁,缠绵而没有尽头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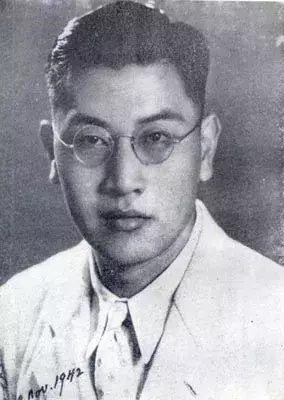
但他还是到了,在施蛰存的家门口停下,然后敲了敲门。

开门的是一个明媚俏丽的姑娘,她就是施蛰存的妹妹,施绛年。
戴望舒望着她,一时有些怔愣,眼前的这个姑娘,脸颊粉嫩,小嘴桃红,青春洋溢,宛如一个纯洁的小天使。
戴望舒的忧郁情绪一扫而光,仿佛看到了太阳底下,最熠熠生辉的一朵娇艳的向日葵,连着心情也积极了起来。
她开口了,微笑着问道:“先生你好,请问你找谁?”
戴望舒反应过来,有些语无伦次地说:“你,你好,,,,我,我找施蛰存先生。”
只听她清脆一笑,说:“原来是找我大哥啊,快进来吧。”
诗人暗暗赞叹,原来施蛰存有这么一个迷人的妹妹。
在施家住下后,戴望舒得以和施绛年有了更多的接触,爱情的幼苗在诗人心里萌生,并且越燃越烈。
恋爱中的人都是诗人,何况对于诗人本人呢。

他把她装进心里,写进诗里,他写道:“我将对你说我的恋人,我的恋人是一个羞涩的人,她是羞涩的,有着桃色的脸,桃色的嘴唇,和一颗天青色的心。”

1928年,一首《雨巷》横空出世,那独自徘徊的行者,和悠扬婉转的情调,以及那个像丁香一样的姑娘,成为了无数人心中谜一样的咏叹调。
丁香姑娘当然就是施绛年。
这首诗是戴望舒的成名作,也是它将戴望舒推向了诗坛新秀的位置,他因此赢得了“雨巷诗人”的雅号。
爱情点燃了他的激情,激发了他的诗情画意,深情不已。
他是快乐的,也是痛苦的。
快乐在于他遇到了,悲伤在于爱而不得,痛苦在于对方好像并不爱自己。
上帝好像并没有想好好地雕塑这位诗人,让他拥有超群的才华,但是却没有诗人的翩翩风度。
他外表高大,但是五大三粗,面孔黝黑黑,还有很多麻点。
他感情深沉而细腻,但同时又冲动抑郁。
他有徐志摩的才情,但是却没有徐志摩的浪漫,他其实有点呆。
这样的男人,是很难讨女人喜欢的。
他,并不是施绛年心中的白马王子。
他们俩性格完全相反,一个是骄阳,一个敏感抑郁到尘埃里。
并且,他比她大5岁,又是哥哥的好朋友,她一直是把他当做哥哥看待的。

但是碍于彼此熟稔,他又是兄长的挚友,尽管绛年不能接受戴望舒的爱,但是却没有明确说明。
她温和平静着,微笑着对待诗人的苦苦追求,希望诗人能明白自己的暗示。
但是陷入爱情中的人,是没有理性可言的, 他仍然勇敢激烈地追求着她。
他继续给绛年写诗:“给我吧,姑娘,那在你衫子下的你的火一样的,十八岁的心。
那里是盛着天青色的爱情的。”
他一心痴迷绛年,铁了心要跟她在一起,终于,他向绛年求婚了。
绛年当然是不答应的,她父母也是极力反对,但是戴望舒竟然以死相逼,正所谓“得之我幸,失之我命”,戴望舒不能想象没有绛年的未来。
绛年被他吓到了,害怕他出什么事,于是暂时先答应了他的求婚。1931年,两人订婚。
但其实,绛年此时是心有所属的,但是恋爱中的人也是自私的,戴望舒看不见,或者假装看不见,他只知道,这么一个可爱的人,他倾尽全力爱着的人,他的一生不能没有她。
但是她明白,她不会跟他在一起。

此时的戴望舒沉浸在喜悦中,他期待着能和心爱的人步入婚姻的殿堂,但是绛年却提出了一个在所有人看来合情合理的要求:戴望舒必须出国留学,取得学位,回来有稳定的收入后,才可能结婚。
很明显这是绛年的缓兵之计,她只能这样做。
尽管戴望舒极其不情愿,但他还是硬着头皮去了法国留学。
为了爱情,为了心中的女神,他情不愿,但是也依然动身了。
在法国,他穷困潦倒,只好一边读书一边译书,并眼巴巴地盼望着施蛰存寄出的稿费。
在法国三年,戴望舒没空写诗,只能尽量想办法赚钱。
施蛰存为了接济他,有时把自己的全部工资都邮到巴黎去了。
他是这段爱情的支持者,一直在极力撮合他和妹妹。
但是他也知道,他不能硬叫妹妹就范,感情的事情,不可勉强。
戴望舒赴法后,绛年就宣布了自己的恋情。
为了不给远在海外的诗人增添苦恼,施蛰存和其他国内亲友一直瞒着诗人。
其实戴望舒在在通信中也能感觉到,绛年的冷淡和拒绝。
他写信给施蛰存询问原因,施蛰存出于好意,也没有告诉真情,只是说“绛年仍是老样子,并无何等恼怒,不过其懒不可救而已。”
但是戴望舒在法国里昂也听到了传闻,思前想后,坐立不安的他,还是决定回国了。
回国后,不得不面临的是残酷冰冷的现实。
果然,传闻是真的,绛年已移情别恋。愤怒的他打了绛年一个耳光,结束了这段长达8年的感情。
没有两情相悦,又怎能开花结果,有的只是徒伤悲。

但是施绛年已经成为了戴望舒一生都无法忘记的景色。
或许是因为真爱,或许是因为爱而不得愈显珍贵,她成了他无法跨越的情感大山,一直在他的世界里停滞不前。
这场不对等的初恋,让戴望舒永坠于悲剧之中。
沉浸在和绛年的失恋中郁郁寡欢的戴望舒,和好朋友穆时英住的很近,看到他如此悲痛欲绝,穆时英将自己的妹妹介绍给了他,以抚慰他爱情中的伤口。
1935年5月的一天,在穆家宽敞的客厅里,18岁的穆丽娟认识了戴望舒。
彼时,他正和自己的哥哥穆时英热烈地讨论着新文学。
早就听哥哥说起过戴望舒和他的诗。
也早就把他那首《雨巷》背得烂熟于心,可当面对眼前那个高大挺拔的身影时,她还是羞涩地低下了头。
正是那不胜娇羞的惊鸿一瞥,秀美典雅的穆丽娟一下子打动了才子戴望舒。
看着她款款身姿消失在客厅的尽头,他的目光迟迟难以收回,她,不就是他梦里寻找千百度的丁香女子么?
穆丽娟的出现,让戴望舒的内心又掀起了狂涛巨浪,他渴望与这个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并结连理。
穆丽娟虽然学历不高,但她非常喜欢文学,对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如数家珍,也非常喜欢戴望舒的诗,甚至能背出戴望舒的每一首诗。
对于一个清纯,秀丽,又仰慕他才华的女孩,戴望舒的痛减轻了很多,终于从感情的困厄中挣脱出来。

戴望舒与第一任妻子
1936年,两人在上海举行了盛大的婚礼。

婚后的生活,曾一度也很幸福,他们在临海的房子里,读书,写作。
读累了就和孩子在花园里开垦,种植。
只是诗人的内心还是对初恋念念不忘,他不知道该怎样爱穆丽娟,只顾自己读书写字,很少与她交流。
穆丽娟苦苦等了5年,也没有等到诗人的爱。
在他为电影《初恋女》写歌词的时候,这种难忘绛年,不满现实妻子的感情表现的尤为强烈,人尽皆知:
“你牵引我到一个梦中,我却在别的梦中忘记你,现在我每天在灌溉着蔷薇,却让幽兰枯萎。”
当时没有人看不出,歌词中的幽兰指的是施绛年,带刺的蔷薇是穆丽娟。
穆丽娟很难堪,心很受伤,她曾经对别人说:“哼,丁香姑娘当然是指施绛年。”
她说:“戴望舒对我没什么感情,他的感情都给施绛年了。”

他们的婚姻就这样冷冷地维持着,事情的导火索是戴望舒阻止穆丽娟回上海,为被特务刺杀的哥哥奔丧。
同年,穆丽娟的母亲病逝,戴望舒又扣下了报丧电报。
当不明就里的穆丽娟身着大红旗袍会见朋友,被笑话说在热孝中还穿大红时,才得知母亲去世的噩耗。
穆丽娟痛不欲生,一怒之下离开了。
他离开时,戴望舒才后悔,他再次以死相逼,写下“绝命书”,然而这次,妻子走的很决绝,没能再回来。
1940年冬,戴望舒无奈离婚协议上签字。
戴望舒无奈的再次陷入爱情的悲剧之中。

经历初恋的失败,第一任婚姻失败的戴望舒,此时对爱情有些心灰意冷,但是命运就是很神奇,安排了他与杨静相识。
杨静和他同在大同图书印务局,她在里面担任抄写员。
两人很快进入了热恋。
尽管杨静的父母竭力反对,但杨静是个充满个性的女孩,她冲破种种阻力,毅然与大她21岁的戴望舒结了婚。
杨静从小长在香港,娇小美丽,活泼好动,结婚时才16岁。

戴望舒与第二任妻子
戴望舒在上段婚姻里吸取了教训,努力不冷落新妻,还为她写诗,说着自己很幸福。
但是两人由于性格和年龄的差异,加之婚前缺乏深入了解,婚后不久便出现了感情上的裂痕,常常因生活上的琐事吵架。
不久,杨静爱上了邻居那热情的有妇之夫,并向戴望舒提出离婚,戴望舒做了种种努力依旧没能挽回这个年轻妻子的心。
戴望舒只得一直不在离婚协议上签字。
杨静无奈之下与姓蔡的青年相偕出走。
至此,戴望舒生命中最后一段婚姻也以失败而告终。
作为爱人,他是失败的,一生的恋情没有一桩圆满。
但是作为诗人,他是成功的。
戴望舒的诗歌作品并不多,而且大多是短诗。
但在诗歌艺术上,却呈现出了独特的成就与魅力。
他是新诗发展的先驱,叶圣陶先生甚至称赞他的诗是中国新诗的“新纪元”。
新诗发展的历史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,多少名噪一时的闻达者随着时光的流逝只剩下文学史价值,不再具备文学本身的价值。
而戴望舒的诗虽几经命运沉浮,却始终魅力不减,风流了几十载。
无论隔着多少时光,读来,都是极美的。

诗歌和爱情相互交织,铺满了戴望舒的一生。
他一生都没走出初恋这条幽深的“雨巷”,那段刻骨铭心的初恋,耗尽了他的爱和幸福。
遗憾的是,在诗人“最后的时间将来的时候”,这三个女人都没在身边。
“垂死的时候”,诗人“虚弱的手”把握的不是任何一段爱情,而是一支针筒。
1950年,新中国刚刚成立的第二年,一天,他为了早日治愈哮喘病,自打麻黄素针时加大了剂量,注射后不久,心脏跳动剧烈,扑在床上就昏迷过去。
等送到医院,已经停止了呼吸。
命运多舛的戴望舒一直在曲折中行走,当曙光照耀他时又过早离世。
卞之琳在悼念文章中说:“望舒的忽然逝世最令我觉得悼惜的是:他在旧社会未能把他的才能好好施展。
现在正要为新社会大大施展他的才能,却忽然来不及了。”